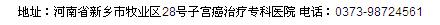林奕含被性侵自杀为什么被性侵后,受害者
每一个文艺而理性的人
都置顶了“周冲的影像声色”
林奕含走了。
那个美丽的、优雅的、青春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26岁时,用上吊的方式,离开这个繁荣又肮脏的世界。
她本可以一生锦绣,一路光明。
本可以洁净地爱,丰盛地生。
一望无际的光明。
漫山遍野的梦……
但一切,都在13岁那年被毁。
13岁,她被补习班老师强暴。
那天,老师说,你的程度这麽好,不如每个礼拜交一篇作文给我吧,不收你周点费。
她听话地下楼了。
老师在家等她。桌上没有纸笔。
成人世界里的肮脏,男人的狂妄和阴险,将童真残酷地撕碎。她千疮百孔。他志得意满,心满欲足。
但她沉默下来。因为他说爱。“我爱你,我喜欢你……我……”
他是远近闻名的人,懂文史,饱读诗书。
她崇拜他。
他以古诗为媒,以美为名义,以爱为借口,甚至以慈悲做托辞,迫害她的身体。
他说:“我是——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在双关小女生的私处。
他说:“你一身都是风景。”——令她悲愤羞惭。
可是,基于自认为脏,基于她觉得自我嫌弃,基于对洁净的爱丧失信心,基于她急需安慰,基于社会对强奸受害者的恶意,基于她认为自己配不上更好的世界,基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沉默下来。
然后,在凶手那里,在深渊里,寻求爱。
她爱上了他。
她甚至想,哪怕是兽性,也只对我一个,我也能心安。
她说,我像只中枪却没被拾走的动物,宁愿被吃,也不愿孤单死去。
但是,他并未停止。他继续寻找猎物,侵犯别的幼女。他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后宫和乐园。
有一次,她亲眼见到他和女生的苟且。
上学期……期末考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小女生。
我在二楼,雨棚如乌云,眼神从佛教哲学的正道溜出去,遥见你颜楷般筋肉分明的步态,她很矮,仰望你,像楚辞的那章——天问。
我可以看见她的脸,鸭蛋脸游离于寤寐,像还在床上,不是眼睛在张望,而是粉红睡痕。
战兢的媚态,我太认识了。
一时间欲聋欲哑。
只恨二楼跳不死人。
但老师说,这是“泛爱”。
他引阿房宫赋:“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
他乐在其中,并流连忘返。
可是,他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去想,之于所有被污的女孩,奸淫留给她们的,是自我怀疑,自我贬低,自我摧残。踉踉跄跄的爱和溃败。支离破碎的尊严。暗无天日的困局。
他不想知道。
他只有兽性。
而他的兽性,都是以文学的名义发生的。
她在脸书上说:
坐拥她们,如果你与文学切割,承认兽性,或许我会好过一点。
但不,你一面念《诗经》,一面插着蒹葭。
抽出来,蒹葭沾着白露。
她终于疯了。
她不再能阅读,所有与文学有关的,都成一种不由分说的、幽暗闪烁的凌辱。
没有人知道,她每天拉开领口,望下看见乳头外一圈齿,想沿着齿痕的虚线剪开,把性征丢掉。
从往昔转来的疼,经过她的肉身,经过她正在摇摇欲坠的灵魂。
医院检测,得到精神病的诊断书。
补习老师当然知晓,但无动于衷,亦无惊无惧无痛。
像与己无关的事情。
像自己毫无罪责,一身无辜。
她被迫休学。
住进精神病院。
在那里,她和一个叫森森的病友在一起,有一回,看见森森脱衣服,一看,她强烈地感到:森森活不久了。
果然,她离开精神病院不久,森森死了。
新闻出来后,电视上给森森打了马赛克,但她依然认了出来。
那时,她还不想死。
她是乖的。
她听话地看书,也听话地“不伤害自己”。
不言不语,不骄不躁,不打不闹。
没人相信她会死。也少有人相信她有病。
学校里的老师们甚至说,“精神病我见多了,没有像你这样的。你是哪里搞来的诊断书?”
而更残酷的是,对于那个怀揣一本被污女生名册的老师而言,女生的自杀,是一种伟大的恭维。
也曾有女生自残。他听了,无愧疚,无不安,反觉得是自我魅力的证明。
哈,居然有人为我要死要活,我真的挺厉害的……
林奕含逐渐绝望。
人生恰如凌迟,每一寸时光,都是酷刑加身,一步步地,将她推到深渊里去。
她说,如果一个女生自杀了你就收手多好。最可怕是,揣着老师的身份,一面吟诗,一面犯罪。
学问何辜?
书页多么清白?
她开始写文章。
她试图用文字自我救赎。
她说,写文章屏蔽又回护官能,伟大的心灵围观、包庇我的噩梦,抬举灵魂,希望臭酸肉体鸡犬升天。
她告诉大家,在被性侵后的日子里,沉默不语,不代表默许,而是在装睡。
云淡风轻,全是墨劓刖宫;
曲意逢迎,尽是笞杖徒流。
26岁的林奕含,在年年2月,出版了个人第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她记录了一切。
小说中,13岁的女主角被补习班老师性侵,最终发疯。
有媒体问:“是你吗?”
她沉默半晌,终于否认。只说:“是真的。由身边人的经历改编……”
3月时,她接受台湾女人迷网站的采访,又说:“但我所知的就是,已经疯了的人,不会变成不疯;已经插入的,不会被抽出来……我所知的就是这样,我非常痛苦非常生气。已经吃进去的药,不会被洗出来。”
同时她也对读者表示:“当你在阅读中遇到痛苦,或不舒服,我希望你不要认为‘幸好是一本小说’而放下它,我希望你与思琪同情共感。”
5月,她自杀。
彻底告别人世。
她离开之后,全民轰动。
她以自己的死,撕破一道口子,将成人世界里的阴暗腐烂,尽数推到我们面前,说:你看,成有的恶,都会有沉默的羔羊来承受。
所有的伤害,都不会消失。
性侵后遗症潜伏多年,最终还是会要人命。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PTSD创伤症后群,即创伤后应激障碍。
个体经历深度创伤后,因种种原因压抑下来,长时间积累,但不会消失。
倘若被某些事件激发,就会造成自伤、自残等应激反应。
林奕含如此。
更多性侵受害者,也是如此。
林奕含不是孤例。
据台湾“卫生福利部”已记录的数据(不考虑隐案率),仅在年,仅台湾就有约人遭受性侵害,其中超过80%受害人都是女性,半数受害人未成年。
在电影《不能说的夏天》中(由真实案件改编),白白是另一个林奕含。
她也被老师性侵(老师同样是多起性侵案的嫌疑人),同样没有控诉。
但是,她在梦里无意识地自杀,她在海浪中无意识地沉溺,她面对喜欢的男生,自觉肮脏,配不上。
更可怕的是,这个社会对她毫无悲悯。
大家说:如果是被性侵,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
她无言以对。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侵犯后,还要靠近恶人。
于是,众叛亲离。
白白母亲骂白白贱货。
林奕含妈妈说,师生恋是女生自己发骚。
她们承受着身体的耻辱,精神上的溃败,舆论上的攻击,亲情上的抛弃,蜷缩在阴暗的角落。
而这种状态,又逼着她更紧密地靠近凶手。
因为只有他一人,不会真正嫌弃她。
林奕含与白白的悲剧,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
罪犯的奸恶,家庭的冷漠,父母的失职,性教育的缺乏,社会文化的扭曲,舆论的嗜血性和嗜腥性,民众的偏见,心理救助的不完善,取证艰难,保护系统不完善,诱奸犯难以被绳之以法……
种种因素导致,性侵的罪行,竟由受害者来承担。
因此,林奕含才悲哀地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比越战更甚。
比集中营更甚。
比核爆更甚……
但这种“大屠杀”不会停止。
它会改头换面,在中国,在北上广,在城市,在农村,在你我身边,继续上演。
如何面对,成了最最重要的问题。
你当然不能奢望人间都是天使。
恶魔更不可能良知发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都是童话式的幻觉。
恶魔自有自己的哲学,可以合理化自己的罪行。
因此,在悲剧发生后,他们不会悔过。
他们只会反思:该如何更便捷,更保险,更滴水不漏,更不为人知,更能逃脱指摘和避开罪责?
于是,恶魔会更用心地打造假象,用文字来化妆,用才华做迷香,用谎言挖陷阱,用名声与钱财做诱饵……让更多女孩跳进去,成为他的猎物。
我们能做的,不是祈祷,也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给罪恶更多笼子、绳索和刀;
给女孩更多保护;
给性侵受害者更多善意;
给儿童带去更多科学的性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可以,那不可以。另外,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会保护你,爱你。
给孩子说“不”的权利,并尊重这个权利;
给凶手更公正的制裁;
给罪行以不容忍,给强奸以不辜息。
给受害者更专业的心理救助。
给女孩更多爱:亲爱的宝贝,生命远比贞操重要。我们爱的,是一个真实的你,而非想象的完美儿童。
如果发生不测,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转发起来吧
让悲剧少一些
让罪恶少得逞一些
赞赏
人赞赏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