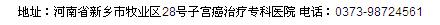经典主义苏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1
子应该怎样度过,而你到现在都还没说出任何主意。”妻子抱怨道。
“你根本就是在说梦话。”岳父也帮腔。
“我还能说什么,既然你们都想迁移,那就迁移吧。我一直反对迁移,那是因为我们对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一无所知。要是祖父还活着,他是不会同意迁移的。战争结束的那一年,祖父把森林和工厂卖给了别人,转让手续也不齐全,现在这些土地到底属于谁?由谁在管理?等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又是在谁的政权之下?”
“你们时常会提到米库利钦这个人,觉得他就是救世主。但是你们怎么知道他还活着,并且还住在瓦雷金诺?你们也就是听祖父说过他的名字而已,对于这个人,你们还了解什么?”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迁移,我也只能同意。现在我就出去打听打听。”
2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来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
为了使外出的人流速度减慢,直穿大厅的小通道两边加上了栏杆。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停地翻身、咳嗽、吐痰,说话的时候,语调都特别高,丝毫不顾及巨大回声对旁人的影响。
医院超员,这些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一过危险期,医院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医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前也是要这样处理这些情况的,但是他不曾知道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人,而车站,俨然成了他们最好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开一个出差证明,现在车次很少,不花钱是走不了的,需要打点(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捻了捻)。”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
3
这期间,岳父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由此,两个人都得到了当时的最高奖赏——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卷。内部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岳父穿过了教堂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了一个地下室,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在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放了一个长柜台。一个神气的保管员站在旁边,不紧不慢地分发着东西,发过一个,就用手中的铅笔划掉一个名字。中间还离开过,到仓库取货物。领东西的人并不多。保管员看了一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岳父的单子,说:“把你们装东西的口袋拿出来吧。”接着保管员就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了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然后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最后还给了他们两个人各一块用纸包着的东西,他俩打开一看,原来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两个人赶紧把包都搭在肩上准备离开,怕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很不自在了。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十分高兴,像喝醉了似的,不是因为可以好好享受美食,而是意识到他们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冬妮娅的夸奖,让她感觉到他们不是碌碌无为的。4
丈夫和爸爸这几天都穿梭于各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以及现在房子的契约,这时候的冬妮娅则在家里清理物品。她心事重重地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反复掂量着什么要带走,什么不带。最后她只把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了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再和别人做交换。
春风从小气窗吹了进来,带着一点新鲜白面包刚切开的味道。院子里的鸡一直叫个不停,偶尔掺杂着孩子们玩耍的嬉戏声。可能是小气窗开太久的缘故,从箱子里拿出来那些冬天的旧衣服散发出浓烈的樟脑丸气味。
此时的冬妮娅,脑子里不断浮现这些话:“路上要检查的,布匹最好弄成一块一块的,把边缝起来。可以带衣服的料子或者半成品,若是成品衣服,最好是较新的,不值钱且重的东西尽量少带,在路上会是负担。最后决定带走的物品最好打包成我和孩子能拎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是必须要带上的,钱就带20或者40卢布的纸币。证件也要尽快办好才是。”
5
准备出发的前夜下起了暴风雪,漫天飞舞的雪花很快给街道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就像一条白色的床单。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把房子和余下的财物交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年老的夫妇,男人以前是商业部的职员,在此之前,他们曾帮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用旧物换了柴火和土豆,两家由此结识。这时,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领着他们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并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
一切东西均以收拾到角落,家里显得无比冷清,此时的三人相视无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岳母的离去,妻子和岳父也是想起已经过世的女主人来。一想到以后就再也不能回到这个熟悉的家来,三个人的眼泪便在眼眶里面打起转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强忍着眼泪,为了感谢照看房屋的女人,好几次进屋拿出了一些女人饰物赠与她,一次又一次地道谢。这些布匹都是黑底配白格子或白点的,就像是窗户上的镂空方格映在了被雪覆盖的黑暗街道上,纹路如此清晰。
6
天刚亮的时候,还在熟睡当中的其他住户便被一阵喊声惊醒:“大家注意了,格罗梅科一家要搬走了,我们去告别吧!”这是一位叫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极爱凑热闹,她一边挨家敲门,一边扯着嗓门继续喊着。
住户们纷纷开门出来,在台阶上站成了一个半圆形,如同要照集体照一般。他们不住地打着哈欠,佝偻着腰,像是怕披在肩上的衣服滑落下来,一面哆哆嗦嗦地赶紧套上毛毡靴。
马克尔也不知道在哪里寻来的酒,喝的烂醉如泥,瘫倒在楼梯的栏杆上面,像是被砍倒了一样,大家都担心他会把栏杆压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家拒绝了他要送到车站的好意,马克尔生气地离开了。
鹅毛般的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比昨晚更加稠密,在快要落地的瞬间停滞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不要降到地面。
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许多。飞舞的雪花像一条白色幕帘悬挂在街道上空,随风摆动着,和行人的脚混淆在一起,让人们感觉如同原地踏步一般。
街道上还是没有人,就在这时,一辆沾满雪的空马车突然出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家的眼前。满身是雪的车夫很快同意只收取几戈比就可以连人带东西把他们送到车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行李放在马车上之后,说是自己要徒步走到车站。
7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和父亲很快就到了车站,站到了两排木栏里的人群中。现在坐火车都不是从月台上车,需要从离这里差不多半俄里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听说是清理车站周围地面上的冰和垃圾的人手不够,所以机车开不到站台处。
两个孩子没有同妈妈和祖父一起站在队伍里面,而是在出入口的屋檐下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妈妈,怕与大人们走散了。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妈妈在他们的脚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所以他俩身上散发出一股很浓的煤油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赶到车站,就看到妻子朝自己招手,并远远地喊着哪个窗口在办理出差证件,于是,他朝那边走了过去。
“给我看看上面盖的是什么章。”妻子问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即把几张小纸从栏杆后面递了进去。
“看看这些印鉴,这可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一个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后面的人说到。
“一旦拥有这些印鉴,您就可以在旅客车厢分到座位。”此时站在她前面的一个了解甚多的人补充道。
这话一出,立即激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那您恐怕还得多等等,高等车厢可在前面。现在坐车的人这么多,能做到列车的缓冲器上也是极其幸运的事了。
“您别听他们胡说,这位先生,我给你说吧,现在的列车都是混合的,没有单一编组,军人、囚犯、牲口都是一起拉的。你们这些人,不要胡说八道,要给人家讲清楚的。”
“就你聪明,那你为他们接下来的事情想过没有,那节车厢里面坐的可都是部队的水兵,一个个的都有枪,难道他们看不出来这位先生是有钱人?到时候,水兵们抄上家伙对付他,就像拍死一只苍蝇那么容易。”
幸好出现了新情况,才使得这漫无边际的讨论戛然而止。
透过厚厚的窗玻璃,等车的人们把目光投向远处,这么远的距离,显然只能看到铁路上的积雪,雪花在半空中停了一会儿,之后慢慢落了下来,如同水中喂鱼的面包渣。
远处腾起了机车行驶时散出的烟雾,人群中开始慢慢有人朝着那个方向走去,熙熙攘攘,看上去就像是检查枕木的铁路员工。
机车越来越近,排队的人群也开始躁动起来。
“开门,赶紧给我们开门,你们这帮骗子。”人群中有人吼道。大家一拥而上,都靠到了门前。
“看看这些人都干了什么,我们被墙堵住了进不去,就像绵羊一样可怜的站在这里。可那边呢?他们就可以不排队直接进去,人家一会儿可就都上车了!你们再不开门,我们可要砸门了!伙计们,我们大家用力挤吧,最好能把这个该死的门挤破,加油!”
“我说你傻吧,你还不信,你知道那些不用排队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是从彼得格勒押送过来服劳役的。之前被送到了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要被送去东部前线挖战壕。你没看见还有押送队吗?那是害怕路上有人逃跑。”那个了解甚多的人接茬道。
8
日瓦戈一家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他们很幸运,一家人在一起,没有分开。
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妻子和孩子举到了车厢上面,车厢边上的活动拉门太重,没人能打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是头一次做这样的车,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一个人也能在车厢上面自由活动。
一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认为这些车厢就是用来运送牲畜的,在受到剧烈震荡之后必然会垮掉。可在之后的行进中,她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无论是弯道还是岔道,即使改变行进方向,火车也一直在顺顺当当地行驶。
这列火车一共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一家在第十四节),前边车厢是军人坐的,中间则是普通乘客,尾部就是那些服劳役的,可能只有车头或者车尾,亦或是中间的几节可以靠近经过的站台。
中间的8个车厢容纳了接近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职业。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入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鞑靼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修道士。
那些社会的上层人都围坐在烧得通红的小炉子旁,彼此高声交谈着,时而大声地笑起来,因为他们不需要担心什么,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也许在途中就会得到赦免。
剩下的那些人,身上穿着开襟的长袍,或者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打开了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或者门前的横杠上,静静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他们获得赦免。
9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对这个上铺位极不满意,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时,她都会往外看一看,想着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换点什么东西。
这一次也不例外,减速的列车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来这是一个大站,停靠的时间应该不会短。她立马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理了理头发,随即从装东西的口袋里面翻出了一条绣着几只公鸡、几个年轻小伙子以及一些弧形线条、车轮的大毛巾。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醒了,他赶紧从铺位上跳了下来,然后扶着妻子下来。
透过打开的车门,尤里看到外面的树木上压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枝干都被压弯了,好似捧着面包在迎接列车的到来。车还没停稳,那些水兵们就跳下了车,奔向车站拐角的后面,那是一个秘密出售违禁食品的地方。
看着那些身着黑色制服、无檐帽、喇叭裤飞速冲过来的水兵,周围的行人赶紧让出一条道来。
在这个车站拐角后面,来自附近村子的农妇们带来了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奶渣饼。为了保持住这些食物的热气和香味,她们都用缝好的棉套盖住。水兵们一边选着自己喜爱的食物,一边和那些村妇们开着玩笑,逗得她们脸都像罂粟花一样通红。其实她们也很害怕同水兵做这等交易,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是由水兵组成的。
很快,其余的乘客也在列车停稳之后接踵而至。人群开始混杂,村妇们的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故意把那条大围巾搭在肩上,还装作要用雪搽脸的样子,在这些村妇中不停地走来走去。
这时,人堆里不断有人朝她喊着:“嗨,那个从城里来的太太,你想用毛巾和我换点什么吗?”
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装作没有听见,继续和丈夫往前走着。
一个围着黑底红花头巾的女人直勾勾地看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肩上那条毛巾,她快速地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危险之后,走到安东宁娜跟前,掀开自己准备要买的东西上遮住的布,悄声说:“你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吧?我看你俩都快流口水了,别犹豫了,用你的毛巾和我换这半只兔子吧。”
此时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并没有听清楚村妇说的最后一句话,隐约觉得她好像在说自己的毛巾。
村妇补充道:“难道你以为这是狗肉么?这可是我男人亲手猎到的兔子。你还看什么?用毛巾和我换这半只兔子吧。”她拎着那半只从头到尾用油煎过的兔子在安东宁娜面前晃着。
最后两人达成一致,交换成功了,可心里都认为对方吃了亏,自己占了大便宜。安东宁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不应该愚弄这个可怜的村妇。那村妇却是极其满意,赶紧离开了交易的地方,招呼上同样刚做完生意的女邻居,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突然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叫嚷着:“你是想往哪里走啊,先生,你买了我的东西,可是还没给钱呢。站住,你给我站住!哨兵!这里有强盗啊!快来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那个边走边笑、没有胡子的先生买了我的东西没有付钱。”
“就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袖口打了补丁的男人?”
“可不就是他嘛,大老爷们,有人抢东西了!”
“出什么事了?”
“那个男人吃了老太婆的馅饼和牛奶,吃完不给钱就走了。你看这个老太婆哭得多伤心,真可怜啊!”
“不能就这样放过他,应该把他抓起来才是。”
“你们还想抓他?没看见他身上都缠满了绷带,可不是好惹的家伙。”
10
在第十四节车厢也有几个是服劳役的,一个叫沃罗纽克的兵看守着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人是极其引人注意的: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来自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瓦夏·布雷金,是一个小五金店的男学徒,今年才16岁;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一个头发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历经新旧社会的交替。
因为都要去同一个地方服劳役,这些原本不认识的人,路上就彼此熟悉起来。谈话中,出纳发现自己和学徒原来都是维亚特省人,再过不久,火车就将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出纳是马尔梅田市的一个小市民,身材魁梧,留了个小平头,脸上略有些麻子。他身上穿了一件颜色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由于出汗,衣服紧紧贴在了身上,看上去就像是女人穿的紧身裙。他在车厢了很少说话,显得有些迟钝,一直低头苦想,一边还挠着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上面出血才停了下来。
去年秋天,出纳正好在街上遇上了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搜到了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食品供应卡,虽然他没有用这个卡领过东西,可人家就是凭着这个就把他抓起来了。之后,他就和许多也是这样被抓进来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按照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他们这些人要先到沃洛格达,中途回来后再经过莫斯科去往东部战线。
在来彼得堡之前,出纳在路加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善良美丽的妻子。妻子得知他被抓后,直奔沃洛格达,准备把他解救出来。可谁曾想到,两个人的路线竟然完全不一样,最后彼此失去了联系。
来到彼得堡之后,出纳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了。
在被抓之前,他刚和这个女人在街角分开,正准备去另一个地方办事。随着被抓的人群慢慢远去,他好像还能见到那个女人的身影,直到视线慢慢模糊。
佳古诺娃是一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着一双很美的手,每次叹气的时候,她就会把背后那根粗辫子甩到胸前,她很爱出纳,所以自愿随车陪送他。
真不知道这些女人看上普里图利耶夫什么了,除了佳古诺娃,他还在另外一节车厢有个相好,听说叫奥格雷兹科娃。那个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很讨厌她,叫她“大鼻孔”和“喷壶”。
很显然,这两个女人是容不下彼此的,所以都避免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来不到这节车厢来,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她要怎样和出纳见面。或许在大家下车装煤的时候他们彼此能看上一眼。
此岸风月彼岸花
天眼官微
西天禾